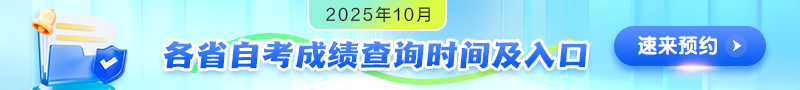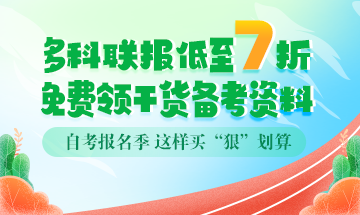自考《古代汉语》全译文(2)
7、《祭十二郎文》——韩愈
年、月、日,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,乃能衔哀致诚,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,告汝十二郎之灵 .
呜呼!吾少孤,及长,不省所怙,惟兄嫂是依。中年兄殁南方,吾与汝俱幼,从嫂归葬河阳。既又与汝就食江南,零丁孤苦,未尝一日相离也。吾上有三兄,皆不幸早世,承先人后者,在孙惟汝,在子惟吾,两世一身,形单影只。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:“韩氏两世,惟此而已!”汝时尤小,当不复记忆;吾时虽能记忆,亦未知其言之悲也。
吾年十九,始来京城。其后四年,而归视汝。又四年,吾往河阳省坟墓,遇汝从嫂丧来葬。又二年,吾佐董丞相于汴州,汝来省吾。止一岁,请归取其孥。明年丞相薨,吾去汴州,汝不果来。是年,吾佐戎徐州,使取汝者始行,吾又罢去,妆又不果来。吾念汝从于东,东亦客也,不可以久。图久远者,莫如西归,将成家而致汝。呜呼,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!吾与汝俱少年,以为虽暂相别,终当久相与处,故舍汝而旅食京师,以求斗斛之禄。诚知其如此,虽万乘之公相,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!
去年孟东野往,吾书与汝曰:“吾年未四十,而视茫茫,而发苍苍,而齿牙动摇。念诸父与诸兄,皆康强而早世,如吾之衰者,其能久存乎?吾不可去,汝不肯来,恐旦暮死,而汝抱无涯之戚也。”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,彊者夭而病者全乎?呜呼!其信然邪?其梦邪?其传之非其真邪?信也,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?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?少者彊者而夭殁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?未可以为信也,梦也,传之非其真也,东野之书,耿兰之报,何为而在吾侧也?呜呼!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!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!所谓天者诚难测,而神者诚难明矣!所谓理者不可推,而寿者不可知矣! 虽然,吾自今年来,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,动摇者或脱而落矣,毛血日益衰,志气日益微,几何不从汝而死也?死而有知,其几何离?其无知,悲不几时,而不悲者无穷期矣!汝之子始十岁,吾之子始五岁,少而彊者不可保,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?呜呼哀哉!呜呼哀哉!
汝去年书云:“比得软脚病,往往而剧。”吾日:“是疾也,江南之人常常有之。”未始以为忧也。呜呼!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?抑别有疾而致斯乎?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,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,耿兰之报无月日。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,如耿兰之报,不知当言月日;东野与吾书,乃问使者,使者妄称以应之耳。其然乎?其不然乎?
今吾使建中祭汝,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。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,则待终丧而取以来;如不能守以终丧,则遂取以来。其余奴婢,并令守汝丧。吾力能改葬,终葬汝于先人之兆,然后惟其所愿。呜呼!汝病吾不知时,汝殁吾不知日,生不能相养以共居,殁不能抚汝以尽哀,敛不凭其棺,窆不临其穴,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,不孝不慈,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,相守以死,一在天之涯,一在地之角,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,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。吾实为之,其又何尤!彼苍者天,曷其有极!
自今以往,吾其无意于人世矣,当求数顷之田于伊、颍之上,以待余年。教吾子与汝子,幸其成;长吾女与汝女,待其嫁。如此而已!呜呼!言有穷而情不可终,汝其知也邪?其不知也邪?呜呼哀哉,尚飨!
「译文」
某年某月某日,叔父我听说你去世消息的第七天,才能满怀悲哀向死者表达内心的感情,派遣建中(韩家仆)打老远赶去备置些和于时令的祭奠时的供品(奠:动词作名词,祭祀时的供品),告慰你十二郎的灵魂。
唉!我幼年丧父,等到长大,不清楚所依靠的人(指父亲),只依靠哥哥嫂嫂。哥哥中年时死于南方(韩愈当年十岁),我和你都年幼,跟随嫂嫂护送哥哥的灵柩到河阳安葬。过后又和你到江南谋求生活(韩氏有别业在宣州,建中二年,藩镇割据势力反叛,中原战乱频繁,时韩愈年十四,随嫂迁家宣州),虽然零丁孤苦,从来没有一天相互分开。我上面有三个哥哥(除韩会、韩介之外,韩愈可能还有一个夭折的哥哥),都不幸过早地去世。继承祖宗后嗣的,在孙子辈中只有你一个,在儿子辈中只有我一个,子孙两代中都是一个男丁,孤独冷落。嫂嫂曾经一手抚摸你、一手指我说:“韩家两代人,惟有你们了。”你当时(比我)更小,应该没留下什么记忆;我当时虽然记得,也不懂嫂嫂的话有多么悲酸啊。
我十九岁那年,初次来到京城(长安)。此后四年,我回乡看望你。又过了四年,我往河阳看望先人的坟墓,正遇上你护送我嫂子的灵柩前来安葬。又过了两年,我辅佐董丞相(董晋)在汴州,你来看望我。留了一年,要求回去接妻室子女。第二年董丞相去世,我离开汴州,你没能来成。这一年(贞元十五年),我在徐州赞佐军务,派去接你的人刚刚出发,我又去职离开了徐州,你又没有来得成。我考虑到,你如果跟着我到东边汴州、徐州这样的地方,那终究还是异乡客地,不能久住。作长远打算,不如西归(韩愈离开徐州后,西归洛阳),打算把家安顿好而使你来到。唉呀!谁料想你突然离开我去世了呢?我和你都年纪不大,以为尽管暂时相互分离,终当长久在一起生活,所以丢下你在异乡谋生于京城,以求得微薄的俸禄。如果确实地知道是会样的结局,即便朝廷的更高职位,我不会一天中断和你在一起的生活而去就任啊!
去年孟东野前往潥阳,我写信(捎)给你说:“我论年纪还不到四十岁,视力却已模糊不清,两鬓花白,牙齿摇晃。想到父亲及伯叔与几位兄长都身体健康强壮,却都过早地逝世,像我这样衰弱的人,难道能够长久生存吗?我不能离开长安,你也不肯来,我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死去,使你陷入无穷无尽的悲痛啊!”谁料年轻的先死而年长的还活着,强壮的过早的去世而病弱的保全了呢?唉!难道果真如此吗?难道是梦吗?难道是传来的消息不确实吗?如果是真的,我哥哥这样有盛美德行的人竟然这样早早地便失去了他的后嗣吗?你这样纯正聪明,反而不能承受你父亲的福泽吗?年轻的强壮的反而夭亡,年长的衰弱的反而存活保全吗?如果不是真的,如果是梦,如果传来的消息不可信,东野的来信,耿兰发来的讣(念作“富”)报(报丧的信),为什么会在我的身边啊?唉!这是可信了!我哥哥的美好德行却使他的子嗣夭亡了!你纯正聪明应该继承你父亲的家业却不能蒙受祖上的恩泽了!所谓天意实在难以预测,所谓神旨难以明白了!所谓天理无法推断,而寿命无法知道了! 虽然如此,我从今年以来,花白的头发有的已经全白了,动摇的牙齿有的已经脱落了,毛发气血一天比一天加重衰弱,精神一天比一天加重微弱,还能有多少时间不跟在你后面而死呢?人死后如果有知,我们又还能分离多久呢(意谓如果人死有灵,我们将很快在地府再相见)?如果人死后什么也不知道了,那么,悲痛的时间不会再有几天,而不再有悲痛的时间将无穷无尽了!你的儿子才十岁,我的儿子才五岁,年轻并强壮的都保不住,这样的小孩儿又能期望他们长大成人吗?唉呀伤心啊!唉呀伤心啊!
你去年来信说:“近来得了软脚病,时常加重。”我说:“这种病,江南人常常有它。”未曾把它看成是件值得忧虑的事。唉!难道竟然是因为这种病而葬送了你的性命吗?或是另外有什么病而至于这样呢?患重病而无法挽救呢?你的信是六月十七日写的(指死者更后写给韩愈的一封信),东野来信说你死于六月二日,耿兰报丧的信没有写你死于哪月哪日。大约东野的信使不知道向家人问明死期,像耿兰发来的讣报一样,不知道应当说清楚死丧的日期,东野给我写信,于是问使者,使者随口乱说应付孟东野的询问。是这样呢?还是并非如此呢?
如今我派遣建中祭奠你,慰问你的孤儿(幼年丧父的孩子)和你的奶妈。他们如果有粮食可以等待守满丧期(古代父亲死后,儿子须守丧三年),就等到丧满以后接他们来;如果不能守满丧期,立即把他们接来。其余男女仆人,全部守护你的丧期。等到我有力量改葬时,终究要安葬你在祖先的坟地,然后奴婢的去留任他们自愿。唉!你生病我不知道时间;你去世我不知道日期,你活着的时候不能和你相互照料着一起居住,你死后又不能抚摸你的遗体倾尽心中的悲哀,自己不能亲自在场为你入敛(给死者穿好衣服装入棺中),下葬时自己不能在场向着墓穴哀哭(窆:把灵柩放入墓穴),我的行为对不起先人的神灵而使你过早地去世,我不孝顺(对不起父辈)不慈爱(对不起十二郎),因而不能与你相互扶持着生活,相互守护着死去,一个在天涯,一个在地角。活着的时候,你的影子不能与我相互陪伴,去世以后,你的灵魂不能与我在梦中相见。实在是我自己造成这种状况,难道又怨谁?苍天啊,(我的悲痛)什么时候才是尽头(曷:疑问代词,多询问时间)?
从今以后,我对人世间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了,只求数顷田在伊水、颍水岸边,来度过晚年。教育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,希望他们成才;抚养大我的女儿和你的女儿,等待她们出嫁:如此罢了!唉!话有说尽的时候,而悲痛的心情却是没有终结的,你是能够理解呢?还是不知道呢?唉呀伤心啊!请享用(这些祭品)吧!
8、《送薛存义序》——柳宗元(唐)
河东薛存义将行,柳子载肉于俎,崇酒于觞,追而送之江浒,饮食之。且告曰:“凡吏于土者,若知其职乎?盖民之役,非以役民而已也。凡民之食于土者,出其什一佣乎吏,使司平于我也。今我受其值怠其事者,天下皆然。岂惟怠之,又从而盗之。向使佣一夫于家,受若值,怠若事,又盗若货器,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。以今天下多类此,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,何哉?势不同也。势不同而理同,如吾民何?有达于理者,得不恐而畏乎?”
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,早作而夜思,勤力而劳心,讼者平,赋者均,老弱无怀诈暴憎,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,其知恐而畏也审矣。吾贱且辱,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,于其往也,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。
「译文」
河东人薛存义将要启程(指在零陵离任时将要启程),我准备把肉发放在俎(古代祭祀或设宴时用来陈置祭品或食物的一种木制礼器)上,把酒斟满酒杯(崇:充实,充满,这里指注满),追赶进而送到江边,请他喝,请他吃(即为他饯行),并且告诉说:“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,你知道地方官的职责吗?(盖:语气副词,表委婉推测语气)老百姓的仆役,并不是来役使老百姓的(而已:用于句末相当于句末语气词”耳“,表限止语气,肯定陈述的事实只限于这样)。凡是靠土地生活的人,拿出田亩收入的十分一来雇佣官吏,使(官员)负责对我公平办事。现在我做官的接受了老百姓的报酬却不认真给他们办事,普天之下到处那是。哪里只是不认真?而且还要贪污、敲诈等行径。假若雇一个干活的人在家里,接受了你的报酬,不认真替你干活,而且还盗窃你的财物,那么(你)必然很恼怒进而赶走、处罚他。现在的官吏大多是像这样的,而百姓却不敢肆无顾及地把愤怒发泄出来并驱逐、处罚,为什么呢?情势(这是指民与官的地位跟主与仆的地位情况不同)不同啊。地位情况不同而道理一样,对我们的老百姓该怎么办?有明于事理的人,能不惶恐并敬畏吗?”
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两年了。每天很早便起床工作,晚上还在考虑问题,辛勤用力而耗费心血,打官司的都得到公平处理,缴纳赋税的(负担)都均衡合理,老的少的都没有内怀欺诈或外露憎恶的,他的行为的确没有白拿俸禄了(的:的确,真实),他知道惶恐和敬畏也明白无误。我又低贱又耻辱(指被贬谪流放),不能在官员的评议中参与什么意见(幽:昏暗,指昏庸恶劣的官吏)(明:指贤明的官吏),在他临行的时候,因此,赠给酒肉而再加上这些赠言。
9、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——柳宗元
自余为僇人,居是州,恒惴栗。其隙也,则施施而行,漫漫而游。日与其徒上高山, 入深林,穷回谿.幽泉怪石,无远不到。到则披草而坐,倾壶而醉。醉则更相枕以卧, 卧而梦。意有所极,梦亦同趣。觉而起,起而归。以为凡是州之山有异态者,皆我有也, 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,因坐法华西亭,望西山,始指异之。遂命仆人过湘江,缘染溪, 斫榛莽,焚茅茷,穷山之高而止。攀援而登,箕踞而遨,则凡数州之土壤,皆在 衽席之下。其高下之势,岈然洼然,若垤若穴,尺寸千里,攒蹙累积,莫得遁隐。萦青缭白,外与天际,四望如一。然后知是山之特立,不与培塿为类。悠悠乎与颢气俱,而莫得其涯;洋洋乎与造物者游,而不知其所穷。引觞满酌,颓然就醉,不知日之 入。苍然暮色,自远而至,至无所见,而犹不欲归。心凝形释,与万化冥合。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,游于是乎始,故为之文以志。 是岁,元和四年也。
「译文」
自从我成了受过刑辱的人(如同说罪人,作者被贬),居住在此州(永州),经常恐惧不安。在那间暇的时候,就缓步而行,无拘无束地游览,每天与那些同伴登上高山,入深林,沿着迂回曲折的溪涧一直走到它的尽头。幽僻的泉水、古怪嶙峋的岩石,没有一个僻远的地方不曾到达。到后就拨开野草,倒尽壶里的酒喝尽为止。醉了又互相靠在对方身上躺下,躺下便做梦。心里有所向往,连做梦的情趣也是一样的。醒后就起来,起来就回家。认为凡是这个州的山水有奇特姿态的,都为我所拥有、欣赏了,但未曾知道西山的怪异独特。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(元和四年,即公元809年),因为坐在法华西亭(法华寺西面的亭台),瞭望西山,才指着西山觉得它不同寻常。于是令仆人,渡过湘江,沿着染溪,砍伐杂乱丛生的荆棘灌木,焚烧茂密芜乱的野草(茷:草叶多),一直清除到山的更高处才停止。攀援着登上山,两腿伸直岔开坐在地上(形同簸箕状,这是古人不讲礼貌或适意自得,无拘无束的一种坐姿)而玩赏,那么所有几州的土地,都在自己的坐垫下面。它们的高高下下的形势,突露嵯峨的样子、深陷低洼的样子,有的像蚁封(蚂蚁洞口旁边的小土堆),有的像洞穴。看上去似乎只有尺寸般大小的景物,实际上已远在千百里之外,(远处的山川景物全都)聚集收缩,堆叠在眼下,没有什么能隐藏的。萦绕着青山,环绕着白水,极远的地方与天交接,向四面望去,都是一样的。(先登高远望)然后知道这座山的卓然耸立,不与小土丘等同。(这是何等)辽阔广大啊,仿佛已与整个宇宙间的浩气融合为一,哪里还能找到它的尽头?悠然自得地与大自然相交游,而不知道它的尽期。拿起酒杯来倒满酒,东倒西歪,疲乏无力地进入醉境(颓然:形容喝嘴酒时东倒西歪,疲乏无力的样子),不知道太阳落山了。灰暗的暮色,从远处来到,来了什么也看不见了,但还不想回家。思虑停止了,形体消解了(形容超然忘我的一种感觉),与自然万物浑然融为一体(冥合:不知不觉中结合在一起)。然后才知道我过去不曾游赏过(意谓:过去的游算不上真正的游),真正的游赏从这一次才开始。所以为这次游赏写成一篇文章(为:动词谓语,这里是写的意思)(志:记,记载下来稿。这一年,是元和(唐宪宗李纯的年号)四年。
10、郑伯克段于鄢——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
初,郑武公娶于申,曰武姜,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,惊姜氏,故名曰寤生,遂恶之。爱共叔段,欲立之,亟请于武公,公弗许。
及庄公即位,为之请制。公曰:“制,岩邑也,虢叔死焉。佗邑唯命。”请京,使居之,谓之京城大叔。 祭仲曰:“都城过百雉,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,大都不过参国之一,中五之一,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,非制也,君将不堪。”公曰:“姜氏欲之,焉辟害?”对曰:“姜氏何厌之有!不如早为之所,无使滋蔓。蔓,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,况君之宠弟乎?”公曰:“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子姑待之!”
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。公子吕曰:“国不堪贰,君将若之何?欲与大叔,臣请事之;若弗与,则请除之,无生民心。”公曰:“无庸,将自及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,至于廪延。子封曰:“可矣!厚将得众。”公曰:“不义不暱,厚将崩。”
大叔完聚,缮甲兵,具卒乘,将袭郑。夫人将启之。公闻其期,曰:“可矣。”命 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。段入于鄢。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,大叔出奔共。
遂置姜氏于城颖,而誓之曰:“不及黄泉,无相见也!”既而悔之。
颖考叔为颖谷封人,闻之,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,食舍肉。公问之。对曰:“小人有母,皆尝小人之食矣,未尝君之羹,请以遗之。”公曰:“尔有母遗,繄我独无!”颖考叔曰:“敢问何谓也?”公语之故,且告之悔。对曰:“君何患焉?若阙地及泉,隧而相见,其谁曰不然?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:“大隧之中,其乐也融融。”姜出而赋:“大隧之外,其乐也洩洩。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君子曰:颖考叔,纯孝也。爱其母,施及庄公。《诗》曰:“孝子不匮,永锡尔类。”其是之谓乎!
「译文」
(《春秋》记载道: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,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;兄弟俩如同两个国君一样,所以用“克”字;称庄公为“郑伯”,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;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,便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,这么处理含有责难郑庄公的意思)
当初,郑武公在申国(姜姓小国)娶了一名妻子,叫武姜(武表示丈夫的谥号),生下庄公(郑国第三代君主)和共叔段。庄公分娩时脚先出来,武姜受到惊吓,因此取名叫“寤生”,很厌恶他。(武姜)偏爱共叔段,想立他为太子,屡次向武公请求,武公都不答应。
到庄公即位的时候,(姜氏)为叔段请求制这个地方(作为封邑)。庄公说:“制邑,是个险要的城邑,虢叔就死在那里。其他的城邑,我不管您怎么说我都遵命。”(武姜便)请求封给京邑,(庄公答应)让他住在那里,称他(叔段)为京城太叔。 祭仲(郑大夫)说:“大夫的都邑城墙超过三百丈,是诸侯国的祸害。先王的制度规定,王侯子弟的封邑不能超过诸侯国都的三分之一,中都(上大夫的封邑)不得超过五分之一,小都(下大夫的封邑)不能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,京邑的城墙不合限度,不是先王规定的制度,您将不能忍受。”庄公说:“姜氏想要,母命不可违,我怎么避除祸害呢?”祭仲回答说:“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?不如早点给他安排个地方,别蔓延开来,就难以对付了。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除掉,更何况您的处居尊位的弟弟呢?”庄公说:“多做不合道义的事情,必定会自己摔跟头,你姑且等着瞧叔段终将垮台的后果!”
事后不久,太叔段使西边边境上的城邑和北边边境上的城邑从时从属(两方)于自己。公子吕(郑国大夫)说:“国家受不了分裂的状况,您打算怎么来对付呢(若之何:对他怎么办?)(若……和:是一种固定格式)?如果打算把国家大权交给大叔段,那么就请让臣下去侍奉他;如果不给,那么就请除掉他。不要使人民产生二心。”庄公说:“不用(指现时用不着动手),他将自己走向灭亡。”叔段又收取原先分属于自己的地方作为自己独占的城邑,(其势力范围)到达廪延。子封(即公子吕)说:“可以动手了!领土扩大,他将获得更多的民众。”庄公说:“多行不义,别人就不会亲近他,土地虽然庞大,也会垮台。”
叔段修葺城廓,聚集民众,修缮武器,准备军队,将要偷袭新郑(郑国都城名)。武姜打算为他开城门(即作内应)。庄公得到情报叔段袭郑的日期,说:“可以出击了。”命令子封率领车二百辆战车连同配套的马匹士卒讨伐京邑。京邑的士民背叛共叔段。共叔段逃到鄢邑。庄公讨伐叔段于鄢城。五月辛丑(隐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,即公元前722年),叔段出走逃向共国。
随后放逐武姜于城颖(郑邑名),并且对她发誓说:“不到黄土下的泉水,不再见面!”发誓后不久,庄公又对此事感到后悔。
颖考叔(郑大夫)是颖谷(地名)封人(镇守边疆的官职),听到这件事,有东西献给郑庄公。庄公赏赐给他酒肉,(颖考叔)进食时把肉放在一边。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,颖考叔答道:“小人有个老娘,我吃的东西她都尝过,只是不曾品尝过君王宫中带汁的肉食,请允许我带回去给她吃。”庄公说:“你有个母亲可以孝敬,唯独我偏偏没有!”颖考叔说:“冒昧地问一下您说的是什么意思?”庄公告诉他缘故,并且告诉他后悔的心情。颖考叔答道:“您在这件事上忧虑什么呢?如果挖掘土地达到泉水,从隧道中想见,谁说不是这样呢(按,既可母子相见,又不算违背誓言)?”庄公依了他的话。庄公进入隧道赋诗:“大隧道之中相见,那快乐啊!真是暖融融的。”姜氏走出隧道进而赋诗:“大隧道之外相见,多么快乐啊!”从此作为母亲和儿子像当初一样。
君子(作者自指)说:颖考叔,笃厚的孝子啊。敬爱他的母亲,(把这份孝心也)延伸到庄公身上了。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篇说:“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,长久地赐给你(指孝子)的同类(锡:赐)。”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!
11、《公孙无知之乱》——《左传》
齐侯使连称、管至父戍葵丘。瓜时而往,曰:“及瓜而代。”期戍,公问不至;请代,弗许;故谋作乱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,生公孙无知,有宠于僖公,衣服礼秩如适。襄公绌之。二人因之以作乱。连称有从妹在公宫,无宠。使间公,曰:“捷,吾以女为夫人。”
冬十二月,齐侯游于姑棼,遂田于贝丘。见大豕,从者曰:“公子彭生也。”公怒,曰:“彭生敢见!”射之。豕人立而啼。公惧,坠于车,伤足,丧屦。反,诛屦于徒人费。弗得,鞭之,见血。走出,遇贼于门,劫而束之。费曰:“我奚御哉!”袒而示之背,信之。费请先入。伏公而出,斗,死于门中。石之纷如死于阶下。遂入,杀孟阳于床。曰:“非君也,不类。”见公之足于户下,遂弑之,而立无知。
初、襄公立,无常。鲍叔牙曰:“君使民慢,乱将作矣。”奉公子小白出奔莒。乱作,管夷吾、召忽奉公子纠来奔。
初,公孙无知虐于雍廪。九年春,雍廪杀无知。夏,公伐齐,纳子纠。桓公自莒先入。秋,师及齐师战于乾时,我师败绩。公丧戎路,传乘而归。秦子、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,是以皆止。
鲍叔帅师来言曰:“子纠,亲也,请君讨之;管、召、仇也,请受而甘心焉。”乃杀子纠于生窦。召忽死之。管仲请囚,鲍叔受之,乃堂阜而税之。归而以告,曰:“管夷吾治于高傒,使相可也。”公从之。
「译文」
齐襄公派遣连称、管至父(都是齐国大夫),瓜熟季节(大约当夏历七月)前往,说:“至明年瓜熟季节派人替换戍防。”一周年戍守,齐侯通知替换戍防的信息不到达;请齐后派人替换,不允许;所有谋划作乱。僖公(襄公之父)的同父又母的胞弟叫夷仲年(夷是其字,仲是排行,年是名)生下公孙无知(襄公堂弟)(春秋时诸侯的庶子叫公子,公子之子叫公孙),得到僖公宠信,贵族享受的待遇级别如正妻所生长子,襄公贬低他(不让他再享受原先的礼遇)。连称和管至父投靠他作乱(以:连词)。连称有同祖父的妹妹(即堂妹)在诸侯国君的宫里(表示做国君的妾),不得宠。使她伺其间隙探听消息,公孙无知说:“事成,我以你为诸侯正妻。”
冬十二月(此为周历,当夏历十月),齐侯游乐于姑棼,随即田猎于贝丘。发现大野猪,随从说:“是公子彭生(襄公派其杀鲁桓公,以掩盖他与其妹,亦是鲁桓公之妻私通之事,后彭生也被杀)。”襄公怒,说:“彭生竟然敢出现!”射他。野猪像人一样站立着大叫。襄公害怕,坠落车下,伤了脚,丢失鞋子。返回,令侍人费其找鞋,没有得到,鞭打他,见血。走出来,遇见造反者(即公孙无知的党徒),胁迫捆绑他。费说:“我哪里会抵抗你们呢?”脱下衣服让人看自己的背,(众人)相信了他。费请求先入宫作内应。把襄公掩藏起来,费与叛乱者打斗,死在门内。石纷如(襄公的小臣)堂前的台阶下(按,叛乱者从外入内,徒人费战死于大门口,石之纷入继而战死于堂前,表示叛军即将入室)。随即进入,杀孟阳(也是小臣,装襄公)于床,说:“不是君主,不像。”发现襄公的脚在侧室门下,随即杀他,而拥立公孙无知。
当初,襄公在位,言行多变,政令不信。鲍叔牙(齐大夫,是公子小白之傅,负责辅佐小白)说:“国君役使臣民的态度轻慢,叛乱将要发生了。”事奉公子小白出宫投奔莒(赢姓小国)。叛乱发生,管夷吾(齐大夫,公子纠之傅)、召忽事奉公子纠投奔鲁国(《左传》是鲁国史官所作,故称“来”。按,公子纠母亲是鲁君之女,所以投奔外家)
当初,公孙无知暴虐于雍廪。九年春天,雍廪人杀无知。夏天,鲁庄公讨伐齐国,送子纠入齐当国君。齐桓公(即小白)自莒先回到齐国。秋天,鲁军与齐军(齐桓公所帅)交战于干时(齐国地名),鲁军军队崩溃。鲁庄公丢失了兵车,改乘其他的车子回国。秦子、梁子(庄公的御者和戎右)打着庄公的旗帜躲在下道上(按,这是为了诱骗齐军,掩护庄公逃跑),因而都走不脱(指被俘)。
鲍叔率领军队来言说:“子纠,是亲属,请君主诛杀他(子纠是齐桓公的亲兄弟,不便由齐国来处死,所以请鲁君杀死他);管仲、召忽都是齐桓公的仇人,希望得到活人,送回齐国处死,才能甘心。”于是杀子纠在生窦(地名)。召忽为之而死(指自杀)。管仲请求受俘,鲍叔接受他,到了堂阜(地名)便解脱他的桎梏(税:通“脱”)。回去把这件事告诉齐桓公(以:介词,省宾语),说:“管夷吾治国的才干与高傒(齐卿)不相上下,用以辅佐可以。”齐桓公听从他。
12、《鞌之战》——《左传》
孙桓子还于新筑,不入,遂如晋乞师。臧宣叔亦如晋乞师。皆主郤献子。晋侯许之七百乘。郤子曰:“此城濮之赋也。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,故捷。克于先大夫,无能为役,请八百乘。”许之。郤克将中军,士燮佐上军,栾书将下军,韩厥为司马,以救鲁、卫。臧宣叔逆晋师,且道之。季文子帅师会之。及卫地,韩献子将斩人,郤献子驰,将救之。至,则既斩之矣。郤子使速以徇,告其仆曰:“吾以分谤也。”
师从齐师于莘。六月壬申,师至于靡笄之下。齐侯使请战,曰:“子以君师辱于敝邑,不腆敝赋,诘朝请见。”对曰:“晋与鲁、卫,兄弟也。来告曰:‘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。’寡君不忍,使群臣请于大国,无令舆师淹于君地。能进不能退,君无所辱命。”齐侯曰:“大夫之许,寡人之愿也;若其不许,亦将见也。”齐高固入晋师,桀石以投人,禽之而乘其车,系桑本焉,以徇齐垒,曰:“欲勇者贾余馀勇。”
癸酉,师陈于鞌。邴夏御齐侯,逢丑父为右。晋解张御郤克,郑丘缓为右。齐侯曰:“余姑翦灭此而朝食!”不介马而驰之。郤克伤于矢,流血及屦,未绝鼓音,曰:“余病矣!”张侯曰:“自始合,而矢贯余手及肘,余折以御,左轮朱殷,岂敢言病。吾子忍之!”缓曰:“自始合,苟有险,余必下推车,子岂识之?然子病矣!”张侯曰:“师之耳目,在吾旗鼓,进退从之。此车一人殿之,可以集事,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?擐甲执兵,固即死也。病未及死,吾子勉之!”左并辔,右援枹而鼓,马逸不能止,师从之。齐师败绩。逐之,三周华不注。
韩厥梦子舆谓己曰:“旦辟左右!”故中御而从齐侯。邴夏曰:“射其御者,君子也。”公曰:“谓之君子而射之,非礼也。”射其左,越于车下;射其右,毙于车中。綦毋张丧车,从韩厥,曰:“请寓乘。”从左右,皆肘之,使立于后。韩厥俛,定其右。逢丑父与公易位。将及华泉,骖絓于木而止。丑父寝于轏中,蛇出于其下,以肱击之,伤而匿之,故不能推车而及。韩厥执絷马前,再拜稽首,奉觞加璧以进,曰:“寡君使群臣为鲁、卫请,曰:‘无令舆师陷入君地。’下臣不幸,属当戎行,无所逃隐。且惧奔辟而忝两君,臣辱戎士,敢告不敏,摄官承乏。”丑父使公下,如华泉取饮。郑周父御佐车,宛茷为右,载齐侯以免。韩厥献丑父,郤献子将戮之。呼曰:“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,有一于此,将为戮乎?”郤子曰:“人不难以死免其君,我戮之不祥。赦之,以劝事君者。”乃免之。
「译文」
齐军:
(主战车)——齐侯(居中指挥)、邴夏(居左御车)、逢丑父(戎右)
(后备车)——郑周父(御车)、菀茷(戎右)
晋军:郤克(中军主帅)、士燮(上军佐)、栾书(下军主帅)、韩厥(司马)
(一号车)——郤克(居左主帅)、解张(居中御车)、郑丘缓(戎右)
(二号车)——韩厥(居中御车,本应为左)、(车左坠车)、(车右倒在车内)
(三号车)——綦毋张(车损,搭二号车,韩厥使之从身后)
孙桓子(卫大夫,为了救鲁国而帅师攻齐,失败后)返回新筑(卫邑)。不入新筑,随后往晋国求救兵。臧宣叔(鲁大夫,齐伐鲁)也到晋国求救兵。都投到郤献子门下(郤克三年前出使齐国,因跛脚遭齐顷公之母萧同叔子的耻笑,曾发誓要报仇,所以鲁、卫求兵都来找他)。晋侯(晋景公)答应给他七百辆战车的兵力。郤子说:“这是城濮战役(632年晋与楚在城濮交战)所用的军额。有已故的前代国君(晋文公重耳)与已故的卿大夫(在城濮战役中立有功勋的先轸、狐、偃、栾枝等人)的敏捷,所以才取得胜利。我跟先大夫相比,不能胜任(用七百乘取胜)这样的战事。请求八百乘战车。”答应他。郤克为中军主帅,士燮以上军佐的身份率领上军(荀庚因故未能出征),栾书为下军主帅(公元前633年,晋国建立三军,称中军、上军、下军。各军都有主帅和副帅,叫将、佐,由六卿担任)。韩厥(卿大夫)为司马(职官名,掌军法),去救鲁、卫两国。臧宣叔迎接晋军,为他们引路。季文子(鲁大夫)帅军与晋军相会。到达卫国境内,韩献子按军法处死部下,郤献子驱车奔驰,想要救他。到达后,却已经处死了。郤子索性以首级示众,高诉他的仆从说:“我以此(替韩厥)分担背后的指责。”
(晋军)跟踪齐军到莘(卫邑,齐师伐鲁,败卫而归,晋师跟踪至此)。六月十六日到达靡笄山下。齐侯(齐顷公)派人挑战,说:“您率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国的土地,敝国的兵力不雄厚,请明朝相见(以上几句挑战的话使用外交辞令,表面上很客气,骨子充满着火药味)。”回答说:“晋国与鲁、卫两国,互为兄弟(都是姬姓国)。他们来告诉说:‘齐国老是到敝国的土地上发泄不满。’我们的国君(晋景公)不忍心,派我们这班臣子来向大国请求,同时又不让我军滞留在贵国的土地上(这里是委婉语,意思说让我们速战,一决胜负)。能进不能退,齐君不会有命令(挑战命令)落空的事情出现(委婉语,说明明朝我们一定奉陪)。”齐侯说:“您答允交战,固然是我的愿望;如果不答允,也一定要交战的。”齐国的高固(齐大夫)徒步闯入晋军,举起石头掷人,擒获晋军的人登上他们的战车,把桑树根系在车上,作为战利品的标志。以让齐营的众人都看见,说:“想要勇气的人尽管来买我多余的勇气!”
公元前589年六月十七日,齐、晋双方军队在鞌摆开阵势。邴夏为齐侯驾车,逢丑父当为戎右(古代战车,将领居左,御者居中。如果将领是君主或主帅则居中,御者居左。负责保护协助将领的人居右)。晋国的解张为郤克驾车,郑丘缓当戎右。齐侯说:“我姑且消灭了这些人再吃早饭。”不给马披上甲就驱马奔驰(之:指驾车的马)。郤克被箭射伤,血流到了鞋上,没有中断擂鼓,说:“我受重伤了(古代病重、伤重、饥饿、劳累过度造成体力难以支持,都叫‘病’)。”解张说:“从一开始交战,箭就射进了我的手和肘,我折断射中的箭杆继续驾车,左边的车轮都被我的血染成了黑红色,我哪敢说受伤?您(‘吾子’比‘子’更亲切些)忍着点吧!”郑丘缓说:“从一开始接战,如果遇到地势不平,我必定下去推车,您难道知道这些吗?不过您确实伤势很重难以支持了。”解张说:“军队的耳朵和眼睛,都集中在我们的战旗和鼓声,前进后退都要听从它。这辆车上只要还有一个人镇守住它,战事就可以成功。怎么能由于伤痛而败坏了国君的大事呢?穿上盔甲,手执兵器,本来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,伤痛还不至于死,您(还是)努力指挥战斗吧!”解张将右手所持的辔绳并握于右手,腾出右手接过郤克的鼓槌擂鼓。张侯所驾的马狂奔起来(由于单手持辔无法控制),晋军跟随他们。齐军崩溃。晋军追赶齐军,饶着华不注山追了三遍。
韩厥梦见子舆(韩厥父,当时已去世)对自己说:“次天早晨避开战车左右两侧!”因此(韩厥)在战车当中驾车追赶齐侯。邴夏说:“射那个驾车的,是个贵族。”齐侯说:“称他为贵族又去射他,这不合于礼。”(按,乃齐侯愚蠢之举)射他左边的人,坠落车下;射他右边的人,倒在车里。(晋军)将军綦毋张(晋大夫,綦毋氏,名张)失去战车,跟随韩厥,说:“请搭车。”跟在左边或右边,(韩厥)都用肘制止他,使他站在自己身后(按,韩厥由于梦中警告,所以这样做,以免綦毋张受害)。韩厥弯下身子,把倒在车中的戎右安放稳当。逢丑父和齐侯交换位置(这是逢丑父为了保护齐侯,乘韩厥低下身子安放戎右的机会与齐侯交换位置,以便不能逃脱时蒙混敌人)。将要到达华泉(泉水名,在华不注山下)时,(齐侯)两边的(中间两马为服,旁边两马为骖)被树枝等钩住。丑父睡在轏车(一种卧车)里,有蛇从他身底出现,以臂击蛇,手臂受伤却隐瞒了伤情。所以不能推车而被追上。韩厥手持拴马绳站在齐侯的马前(絷:拴缚马足的绳索),拜两拜,然后下跪,低头至地(这是臣下对君主所行的礼节。春秋时代讲究等级尊卑,韩厥对敌国君主也行臣仆之礼)。捧着一杯酒并加上一块玉璧向齐侯献上,说:“我们国君派我们这些臣下为鲁、卫两国求情,他说:‘不要让军队深入齐国的土地。’臣下不幸,正好在军队任职,没有地方逃避隐藏(我不能不尽职作战)。而且怕由于我的逃避会给两国的国君带来耻辱。臣下不称职地处在战士地位,冒昧地向您报告,臣下不才,代理这个官职是由于人才缺乏充数而已(外交辞令:自己是不得已参加战斗,不能不履行职责,来俘获齐侯你)。”逢丑父(充齐侯)命令齐侯下车,往华泉去取水来给自己喝。郑周父驾着齐君的副车,宛茷担任副车的车右,载上齐侯使他脱身。韩厥献上逢丑父,郤克将要杀掉他,呼喊道:“在我以前从来没有代替他的国君承担患难的,有一个在这里,还要被杀死吗?”郤克说:“一个人不畏惧用死来使他的国君免于祸患,我杀了他不吉利。赦免他,用来鼓励事奉国君的人。”于是赦免了逢丑父。